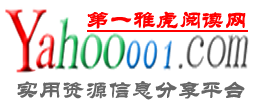《痛,从指尖蔓延》采用倒叙的方式,从取下钢板开始,在这种痛中开始回忆生活中各种的痛。

决定摘掉钢板的刹那,我的心是紧了又紧。
想着这痛跟着我十五年的时间,还在不停地在我身上转变着方式,偶尔,我会处于迷茫的状态。看着已经十五岁的女儿,亭亭玉立地站在离我不远的窗口,或许,一切都是那么的值得,而且无悔……
女儿六个月,我高烧不退,用了很多的药物,终于在一个夏日的凌晨,烧退了,母亲和爱人都笑了。可是,一周以后,我右手的食指开始肿胀,最后像一根小胡萝卜一样粗了。十指连心,指尖的疼痛让我彻夜难眠。每天清晨肿得粗粗的手指,不能弯曲,更是无力去拿东西,我知道,这回是真的“病了”。我不敢去翻书,即使那本内科学就在我床头边的书架上,我还是不愿意去承认这是病,仅仅是一个手指头而已,也许很快会好的。作为医者,我尽量去欺骗自己,吃一些口服的药物去一下表征。果然,症状明显改善,而且那种痛感在减弱。
这样,过了两个月,痛只停顿在手指上,没有加重的迹象。
秋天到了,好像一瞬间窗外的大杨树上的叶子就被大风吹尽了,这个秋天有点寒。
母亲病了。几经周折,确诊以后竟然是“肺癌”。我放下一切,奔跑在各个大医院,尽最大的努力想挽留住母亲……我忘了我的病,它一直跟在我的身后,从指尖开始蔓延,手腕,肘关节,肩关节,然后是膝关节,最后爬上了我的脚。
母亲家住在一楼,进去单元门只有八个台阶,我上去却十分艰难,每次都是忍不住地流汗。
我眼看着母亲被疾病侵蚀着,一点一点地瘦下去,从原来的的一百四十斤,到最后不足八十斤。癌细胞从肺部到淋巴,再到她的盆骨上,病魔在母亲身上次虐,疼痛在我的身上横行,我和母亲头对头地躺着,母亲笑得很勉强,颤抖的声音,让我能感到她身上的痛。
“丫头,别再给我治疗了,你看看你,瘦没了,脸都瘦成一条了。”
“我很好的,不疼的。止痛药吃了很好用的。”我回答母亲时,感觉下颌关节在疼痛,让我的声音也有点变调。
“我活着,你没机会去系统治疗,丫头,我的病我知道,别治疗了。”母亲的声音弱弱的,说话间,就昏睡了过去。
看着母亲就在我的眼前,一点点地倒下去,我的眼睛热热的。我是无能的人,妈妈,我陪着你痛!那时候,经常在夜里,我会被自己的喊声震醒:学医,有什么用?救不了母亲,也救不了我自己!
母亲是安静的,一直到生命的最后。
在一场大雪里,母亲走了。可那彻骨地痛却留在了我的身上,从指端蔓延起来的痛,早已经不满足游走在关节上了,我全身浮肿,翻身都要爱人推上一把,晨僵,让我失去了应急能力,只能慢慢地、挪着步走。
有时候,我很想找一个合适的词汇去形容这种痛,可是没有结果。
我再一次和我的心做斗争,虽然我已经一万次地告诉自己,我真的和一种终身携带的疾病相遇在流年的路口了,可是,我的另一颗心就是不承认这个结局。于是,我去了北京,在协和医院免疫科做了进一步的确诊,事实拆穿了我的谎言,这病,一直在,它的名字就叫“类风性关节炎”,不死的癌症。
那一天,我拿到了确诊的诊断,独自一人在王府井行走,脚下越来越痛,一直走到麻木。我站在玲琅满目的街口,不知所措,那一刻,我已经不在乎痛了,只想着如何去结束这一切……
回酒店的路上,我的脚已经肿得涨出了鞋面,不能系鞋带,走出去时穿的运动鞋,回来成了鞋托。很多时候,我都不敢去想,总觉得有一天我会在行走中突然倒下,如果能追随母亲,或许还是一种幸福,就怕有一天我会卧床,会痛苦地活着……
拿着病历回到了哈医大,我开始了第一次系统治疗。
口服爱若华,静注“氨甲蝶呤”。每一次针头还没拔下来,我已经吐得一塌糊涂,眼泪鼻涕都顺腮而下。那一刻,我在想,或许这种痛苦是让我时时记起失去母亲的疼儿,无限蔓延,直达心底。
我曾经一度消沉过,每天的晨僵使我寸步难行,要连续做上几次深呼吸,才敢抬起腿来走路。最严重的的时候,吃饭也张不开嘴,下颌骨处也被病毒侵蚀着。那一年的冬天,总是在下雪,一场接着一场。房间里,总是见不到阳光跑进来,只有灰蒙蒙的阴郁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久久不散。
我开始恨自己,有的时候想吃药,止住这疼痛,可是抬起手却够不到近在咫尺的水杯。两岁半的女儿,总是会悄悄地把药片和白开水慢慢地放在我的床头桌上。她还不会说安慰的话,或许是因为我一直病着,她有了小大人的目光,虽然怯怯的,但是总能看到一种坚定。
想母亲,特别是痛感急剧增高时。
没妈的孩子橡根草,真的。有时候,我会抱怨父亲的粗心大意,偶尔也会和爱人怄气,他居然一点不知道体贴和疼爱我,让我一直在痛苦中生活。那一刻,我特别想念母亲。想着母亲的慈爱,想着我从小就赖在母亲的怀里……痛在指端,它在无限游走,一直爬到了脚尖。
大量的药物让我脆弱不堪,主治医生再次建议我服用激素,我犹豫再犹豫,还是对疼痛妥协了。因为,我看到了我的女儿,我也是母亲,我要坚持,跟痛相伴着走下去。
激素,对疼痛缓解十分地快速,然而我却十分害怕,担心我的骨骼,在激素的破坏下会不会失去支撑能力,我坚持治疗,如果还是倒下,怎么办?无数个问好在我的脑海里盘旋着。
不过,用上激素,缓解症状却是立竿见影的。
两个月过去了,我竟然可以穿着高跟鞋走出家门了。疼痛再一次从全身减退到我的指端,肿了消,消了肿,如此反复多次。疼痛的局限让我重新扬起了生活的勇气,此时,我已经忘记了激素的副作用,只看到了窗外那抹斜阳。
病人是害怕劳累的,而我,却要感谢劳累。
治疗三个月后,偶然遇见了多年的好友。寒暄几句之后,她觉得我不是病了,而是精神颓废,这个时候需要一种动力去抵抗疾病的蔓延,那就是让自己忙碌起来。我们在小咖啡厅里坐了一个下午,起身时,我竟然迈不开脚步,那僵直的痛感再一次爬上我的心头。我脸上有了惊慌,她却鼓励着我:没问题,痛一下就过去了,闭眼睛,使劲儿迈出去!
我用手搬起了腿,一大步,两大步……走到路中间的时候,痛感消失了。回到家里,我一直在想着朋友的话,或许,这种临床没有办法的疾病,真的是精神治疗比较关键的。
第二天,我来到了朋友的公司,开始了我长达十年的兼职工作。
时光在不经意间滑过,那痛一直缠绕在指尖上,偶尔也会在腕部和肘部,但是,我从不在意,一直坚持复查,坚持治疗,从不间断。五年,当我发现我的掌骨略有发宽的迹象时,和我的主治医生说起来,赵老师笑着说:丫头,你已经是我记录在案,恢复最好的患者了。他顺手递过来的病历让我看,和我一年得病的患者,已经有一半的人开始渐渐地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更不要提工作了。
我知道,你不可能离开我了,于是,我开始不停地说服自己,不就是痛吗?我能坚持!那一刻,我再一次看到了女儿倔强的小脸。
总的来说,我是一个粗枝大叶的女人。因为不在意疾病的存在,我一直也没放弃任何自己喜欢的活动,比如旅行,比如聚会,比如彻夜不眠地看小说,痛一直陪伴着我,而我却把病放下了。
拖着病弱的身体,我几乎走了半个中国,从海南到西安,从云南到香港,再到我的城市的周边,步行、飞机、火车,所有的交通工作都尝试了一遍。某一刻,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胜利者了。
爱人总是开玩笑地对我说:这病,就是耽误你学习开车了,你什么都尝试了,就是开车一直没安排上日程。
一句玩笑话激起了我心底早就在熊熊燃烧的欲望,车,一直吸引着我的目光。
拿到驾驶证时,季节已经滑进了冬天。订车,提车,在几天内就完成了,许多朋友对我都投来了诧异的目光。提车那天下着小雪,下午四点半,正是晚高峰的前奏。我却开始了第一次驾车之旅,车在路上爬行,从4S店到家里,平时只用二十分钟的距离,我开上了一个小时,不过,我确实把车开回了家。
北方的冰雪路面,是开车的难点,我却踏着雪开始的驾车体验。
第一次漂移是在哈尔滨第一坡上,我送孩子去上课,拐进辽阳街,前面的车停了下来,司机是一位大姐。她抱歉地打着手势,拿起电话,在找人来帮她把车开走。我茫然地看着她,她不走,我的车只能倒下去,后面是这个城市有名的“大坡”。挂上倒挡,脚还没离开刹车,车子已经开始下滑,我有点惊慌失措,车速越来越快……我只好点刹。这时,我想起了师傅的话,不要用力去踩刹车,可是,就在那一刻,我已经惊惶无措。
车子瞬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回转,车的前轮顶在了路旁的石基上,停了下来。幸好,是假日的清晨,路上没有行人;幸好,那路基比较矮小,只是挡住了滑行的车轮而没有伤到我的爱车;幸好,女儿一直是一个胆大心细的孩子,这一刻表现得比较勇敢……
第一次驾车远行,好胜心切,我一个人用了七个多小时,把车开到了东宁。到达目的地时,朋友们拉开车门,大声夸赞我时,我的脚却使不上劲儿,僵直着,寸步难行了。返回的途中,我是再也不摸我的车了,只是静静地当着乘客。
十年,我学会了很多,当然疾病也在慢慢进展着。类风湿的病人很忌讳感冒,每一次发烧都会导致病情的加重。我一直偷偷地安慰着自己,我已经好多年远离这流感病毒了。一次单位体检,我发现了我的手臂有了伸直的受限,略微弯曲,虽然不易察觉,但是给采血造成了障碍。不经意的一次意外脚扭伤,迟迟不愈,脚踝肿胀一直持续了两年。
终于,疾病有了一次战绩,它让我倒在了病床上。两年前的扭伤居然给它带来了可乘之机,我的左侧脚踝居然痛得让我下不了地,针刺一样的疼痛,刺激着我的心脏,一阵阵揪心地痛着。
治疗、会诊、专科,一系列的操作有序地进行着。当医生告知我是“类风湿性骨膜炎”,而且骨膜破损严重。我痛定思痛,最终选择了永远放弃,让病痛在这只脚上永远停止。类风湿属于免疫低下型的结蹄组织疾病,我要求做了左踝关节的融合术,把它赶了出去。十三年过去了,我第一次因为旧疾复发住院,一直给我做复查治疗工作的赵主任,看着检验科返回的化验单,欣慰地说道:丫头,你是我治疗患者中最坚强的。类风湿因子31,数据很好,如果不是因为外伤,你会很健康的。他语气着重在“健康”这两个字上,我知道,赵老师仍在给我打气,让我不要和疾病低头。
我知道手术很简单,只是很痛。
术后第一天,我一直望着窗外,这时已经是初春的季节,不过,只有风,没有绿色。疼痛让我的脸变了形,额头上满是汗水。干妈一直问我:痛不痛,我给你打一针止痛药吧。我摇摇头,知道药物也就能止住几个小时的痛,然后还会痛的。
夜里,病区很静,决定手术后,我一直没好好想想,在轮椅上的四个月我应该怎么过?看着带着白色定型的脚具的左脚,刀口是一阵阵钻心地疼痛传遍我的全身,侵占了我的大脑神经。刚要喊痛,我就看到了干妈和爱人疲惫的脸,他们一左一右地靠在病床边。忍,我可以!
一夜未眠的我,在窗外露出灰白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想,我一直想站立成别人眼里的风景。我没有如花的容颜,亦没有高挑的身材,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独自行走的人。可是这一次,我自己驾车来到了松花江边,当我拄着拐走下车时,我想,那一刻我成了别人眼里的一道风景了。
夏日的斯大林公园,绿树遮阴蔽日,有风吹送,显得格外凉爽。拄着拐,没有办法走快,我只好静下来看着一群退休的老人们在凉亭里拉琴唱戏。唱声高高低低地传来,是一曲京剧,字正腔圆,滋味十足。有了一次这样的经历,我不再怕众人的目光,经常会在楼下乘凉,和不怎么相识的邻居们聊一会儿天,没有了最初的尴尬。
带着钢板生活的日子,我一如往日一样。虽然我和治疗的药物始终保持着不离不弃的关系,我依然微笑着。
我开始接受生物制剂的治疗方案,因为手术导致我的免疫力再一次降低了。每周一次皮下的注射,让我对针刺的感觉麻木了。类似于化疗药物的注射剂,让我的三角肌处的皮肤变得有些粗糙,那让我骄傲的细腻也开始远离了。
这时候我结识了小病友——英子,她二十四岁,十八岁发病。英子长得很漂亮,她告诉我有很多男孩子追她,可是她不敢结婚,因为她上网查了资料,类风湿会遗传。我们住在一个病房里,每天晚上,我都会听到她低低的哭泣声,她说,她实在是忍受不了这种疼痛了,五年了,她的眼睛一直是肿着的。英子正值青春好年华,可是因为疾病的折磨,看上去有了几分沧桑,美丽的大眼睛也显得有几分空洞。彻夜难眠,极度疲惫让她的头发枯黄,皮肤干干的,少了许多光泽。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安慰她,因为那痛也一直在折磨着我。
脚上带着沉重的钢板,我不得不辞去了公司的工作,生活变得寂寥而又平静。我拾起了文字。或许在疼痛中书写的文字都带着悲愤与沧桑吧,我居然没写几篇美文就走近了伤痛的回忆中。好多文友说我写的文章过于伤感,尤其是一些亲情文字,这可能也是跟疼痛有关吧。
曾经,我和骨科医生探讨过,骨科的手术之所以让病人产生恐惧是因为它还要有下一次手术跟着,患者无一例额外地要上两次手术台。在休养的两年间,每当疼痛来袭,我的心还会颤抖,大多还是因为脚上的这张钢板。
不过,当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行走在西塘,穿行在鼓浪屿的各个狭窄的街道,登上了黄山,看云起云落时,那疼痛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再一次躺在手术台上,我变得平静了。全麻让我很快进入沉睡中,四十分很快过去了,手术很成功。
蜗居的日子,平静而又有几分恬淡。窗外,一场又一场的雪落了下来。室内,茶香淡淡,那漫过心海的是沾满墨香的文字,虽然还有疼痛伴着我,但是,经过岁月的洗涤,那从指尖漫起的痛早已经成了我对生活的种种感悟……
疼痛,只是一种主观感受,可它给我更多的是一种坚定和战胜疾病的勇气。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3372575805@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yuedu.yahoo001.com/meiwen/1547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