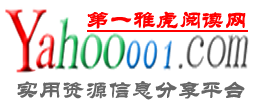齐别根纽·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诗选
齐别根纽·赫伯特,1924年出生于波兰东部洛威尔,曾在华沙学习法律和哲学。虽然他的诗作很早在杂志上发表,但他的第一本诗集《光线的一种和声》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后的1956年才出版。他继而出版了好几部重要的诗集《赫尔墨斯,狗和星星》(1957),《对于客体的一种研究》(1961),《我思先生》(1974),赫伯特也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史论者,并写作广播剧。其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赫伯特的诗歌具有深广的文化和历史视野,风格多变,属于那种在不同时期用不同风格写作的诗人。
一个诗人的重新讲述
(一则广播剧)
荷马:诗是一声喊叫。你知道去掉那种喧嚷之后,一首诗还剩什么?
埃尔派尼:不知道。
荷马:什么也没有。
教授:在米利都附近的安诺尼,米洛的安诺米是巨人旁边的一个聋子。
(从一个水龙头中传来水的嘀嗒声)
……不重要的和常见的主题。安诺米坚持把一首诗奉献给一株柽柳,一棵普通的植物,繁茂和没有用处的。
荷马:我曾经讲述战争
灯塔和船只
被杀的英雄
和杀人的英雄
但我忘记了一件东西。
我曾经讲述海上的风景
城墙的坍塌
大火中的谷物
翻转的土丘
但是我忘记了那株柽柳
当他活着时
用一支矛突围
他受伤的嘴巴
紧闭
他没有看见
那海
那城邦
没有看见朋友
他瞧见了
在他的脸附近
一株柽柳
他目光延伸
至最高处
柽柳的干枯的细枝,
同时避开了
棕色和绿色的叶子
穿越天空
没有翅膀
没有血
没有思想
没有——
教授:主题的没有意义和形式上的堕落齐头并进。
荷马:……在黑暗和沉默中我的身体正在成熟。这多象春天的大地,充满了无法预料的可能性。一层新的茸毛正在覆盖我的皮肤。我开始发现我自己,开始调查和描述。
首先我要描述我自己
从我的头部开始
或者最好从我的手臂
准确地说是左臂
或者从我的手开始
从左手的小拇指
我的小拇指
是温暖的
柔和地向内弯曲
直到一粒指甲
它由三个部分组成
直接从掌心里生长出来
如果和手掌分离
它将变成一条十足的长虫
它是一只特殊的手指
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左手小拇指
径直地被赋予我
其他的左手小拇指
是冰凉的抽象
跟随我
我们有着共同的诞生之日
共同的死亡之日
和一种共同的孤独
仅仅是我的血
捶平来自黑暗的赘述
紧紧拽住那遥远的海岸
用那生存的命脉。
小心翼翼地,我开始调查这个世界。我了解每一桩事情直到它变得无用。象来自另外一出剧情的布景。我必须观察每一件新鲜事物,不是从特洛伊、从阿喀琉斯开始,而是从一只凉鞋,一只有搭扣的凉鞋开始,从小路上无意踢到的一块石子开始。
一块石子是一个活物
十分完美
和它自身相一致
遵守自身的界限
恰如其分地拥有
作为石头的意义
拥有区别于任何事物的香味
从不惊慌也不欲求
它的激情和冷漠
正当并充满尊严
当我把它捏在手中
我感到一种巨大的谴责
它高贵庄严的身体
识破了一种虚假的温暖
石头不可能被驯服
它们将永远望着我们
用一只辉煌而镇定的眼睛
我永远不再回到米利都。那儿是我的喊叫驻留的地方。它会以某些黑暗的小径抓住我并把我杀死。
在生的喊叫
和死的喊叫之间
紧紧地盯着你的指甲
盯着一个落日
盯着一条鱼的尾巴
你将要看到的
不是带到市场上
减价出售的东西
不是喊叫
那些神灵象情人们
象巨大的沉默
在喧闹的开始
和喧闹的结束之间
象一种难以捉摸的旋律
没有声音
又拥有全部的声音
这仅仅是开头。开头总是古怪的。我坐在宙斯神庙最低的一层台阶上,米洛库勒斯和我正在赞美一只小拇指,一株柽柳树、一粒石子。
我从来没有门徒和听众。人们至今对那史诗中巨大的火光感到害怕。但是它正在熄灭。很快那些烧焦的东西将为青草所覆盖。我就是那青草。
有时我想我也许能用新的诗歌吸引新的听众,那将不再是从勇气到勇气,从喊叫到喊叫,从恐惧到恐惧。代之而起的,是从谷物到谷物,树叶到树叶,感情到感情。从词到沉默。
崔卫平 译
声音
我行走在海滩
寻找那种声音
在一道波浪和另一道波浪的喘息之间
但是这儿没有声音
只有水的古老的饶舌
却不风趣
一只白色鸟儿的翅膀
晾晒在一块石头上
我走向森林
那儿保持着
一只巨大的沙漏的微响
将叶片筛选腐土
腐土筛选为叶片
昆虫们有力的嘴巴
吃光大地上所有的沉默
我走向田野
大片的绿色和黄色
被小生物们的腿所粘牢
在与风的每一次碰击中歌唱
在大地无休止的独白里
若有某刻出现停顿
那是这样一种声音
它必定明晰嘹亮
除了私语什么也没有
轻轻的拍击骤然增加
我回到家里
我的经验呈现
进退两难的形状
要不世界是个哑巴
要不我自己是个聋子
但是也许
我们双双
注定陷入苦恼
因此我们必须
手挽手
无目的地继续
走向暗哑的喉咙
从那里升起
一种含混不清的音响
崔卫平 译
我想描述
我想描述最简洁的情感
喜悦或忧伤
它不象其它人所做的
企及太阳或雨水的闪电
我想描述一束光
它诞生于我的内部
但我知道它
并不象任何星光
因为它并非那样明亮
那样纯粹
它并不确定
我想描述勇气
而没有一头落满灰尘的狮子拖在身后
想描述焦躁
而不去摇晃一只盛满水的怀子
以另外的方式
我愿以所有的隐喻
换回一个词
它象肋骨一样出自我的胸脯
换回那个词
它遏制在我皮肤的
界限之内
但虽然这是不可能的
适才说——我爱
我便发疯地四处乱跑
捡拾鸟儿的羽毛
而我的温柔
完全不是用水做成
却向水要求一张面孔
还有愤怒
它不同于火焰
只是借取了火焰
一种啁啾不已的语调
如此模糊
如此模糊
在我内部
有着颇会保养的绅士
永远弃绝的那些
并且说
这是主语
这是宾语
我们躺倒睡去
一只手压在脑袋下面
另一只手伸向一堆星球之中
我们的双脚遗弃了我们
用它们细小的根筋
体验着大地
在下一个早晨
我们痛苦地将其拔出
崔卫平 译
敲击者
有些人脑袋上
长着盛开的庭院
头发里扯出小径
通往洒满阳光和白色的城市
对这些人来说
他们闭上眼睛
想象的瀑布顷刻
从他们的额头流淌下来
我的想象
是一块木板
我的唯一工具
是一根枝条
我敲击那木板
它回应我
是——否
是——否
别人那里是树木绿色的钟声
水面蓝色的钟声
我却拥有一位敲击者
来自无人照管的花园
我捶击那木板
它怂恿我
用道德家枯燥的诗句
是——否
是——否
趣味的力量
这完全不需要伟大的性格
我们拒绝、失望和抵抗
只是拥有一点点起码的勇气
但这主要是一件趣味方面的事情
是的趣味
于其中有着灵魂的质地和良心的软骨
有谁知道我们能否做得更好一些
是想给瘦如薄饼的女人献上玫瑰
还是献给博斯画中迷人的角色
但此时有着怎样的恐怖
可怕的陷阱,谋杀者的小巷、营房
被唤作正义的殿堂
一个土生土长的靡菲斯特穿着列宁装
把奥罗拉的孙辈送往旷野
男孩有着土豆般的脸
丑陋的女孩双手通红
他们的修辞学用廉价的麻袋布做成
(马尔库斯。图勒斯在坟墓中翻转不已)
同义反复的一连串概念象落下来的鞭子
屠杀者的辩证法无理可讲
他们的句法来自主观性的美
因此美学在生活中可能有所帮助
一个人不可能忽略美的学习
在宣布答应之前我们必须仔细审视
建筑的式样,铜鼓和管乐的节奏
办公室的颜色和葬礼的可鄙仪式
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拒绝服从
我们感觉的君王骄傲地选择流放
这完全不需要伟大的性格
我们仅仅拥有一点点勇气
但这主要是一件趣味方面的事情
是的趣味
它要求我们走开,做出一张扭歪的面孔和一种嘲弄
甚至为了这身体上罕见的满足必须
低下头颅
崔卫平 译
普洛克路斯忒如是说
我的流动王国在雅典和迈加拉之间
在那里我独自统治森林沟壑悬崖
没有君王的节杖老年人的忠告仅仅有一根棍棒
仅仅披着一头狼的外衣
我也没有臣民
如果有的话他们不会活得比黎明更长
神话专家们错误地称我为强盗
实际上我只是一个学者和改革家
我真正的热情在于人体测量
我用一个完美的人的尺寸做成一张床
我用这床衡量被捉到的过路人
我不得不——我承认——拉长——一些胳膊和截断
一些腿
接受治疗的病人死去 他们死得越多
我越是确信我的研究是正当的
因此所谓进步不能没有牺牲者
我渴望取消高人与矮人的差异
我想给讨厌的多样化人类单一的式样
为使人们整齐划一我竭尽全力
我的头颅被忒修斯砍去那杀害无辜的诺陶诺斯的凶手
他利用一个妇女的线团逃出迷宫
一个没有原则和前景的聪明人
我有一个切实的希望有人会继续我的劳作
将这个刚开始的如此精彩的事业进行到底
崔卫平 译
为什么是经典
一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四卷书里
修昔底德描述了他失败的远征
在那些围攻、战役、疾病
将领们的长篇讲演
天罗地网
外交谋略当中
这个插曲像森林里的
一枚细针
雅典所属的安菲波利斯
输给了布拉希达斯
因为修昔底德的救援来得太迟
为此他获得了终身流放
从他出生的城邦
整整一生的流放
了解此种代价
二
现今战争中的将领们
在类似的困境中
对他们的屈降信口胡编
夸耀自己的英雄主义
及如何无辜
他们抱怨部下
抱怨嫉妒的同事
和有敌意的风
修昔底德仅仅说
那是冬天
他有七条船
已经开足马力
三
难道艺术的主题
必须变成一只破碎的瓦罐
一个渺小破碎的灵魂
装满自我怜悯
于是给我们留下的
将是情人的眼泪之类
在光线昏暗的小旅馆里
当糊壁纸剥落时
崔卫平 译
我们的恐惧
我们的恐惧
并不套着一件夜晚的衬衫
不具有猫头鹰的眼睛
不是去掀开一只棺材盖子
或熄灭一支尚在燃烧的蜡烛
甚至不具有一张死者的面容
我们的恐惧
是在口袋中发现的
写在纸上的一句话
"提醒伏契克
德劳加街老地方有危险"
我们的恐惧
并不从飓风的翅膀上升起
并不停落在一座教堂的塔尖
它就在现实当中
它有着
用仓促做成的形状
穿着带体温的衣服
拎着口粮
和武器
我们的恐惧
不拥有一张死者的面容
死者对我们温柔的
我们把他们扛在肩上
裹在同一条毯子底下
合上他们的眼睛
摆正他们的嘴唇
挖一个干燥的坑
把他们埋掉
不要太深
也不要太浅
崔卫平 译
舌头
一不小心,我越过她的牙齿,把她那机灵的舌头吞了下去。它现
在长在我身体内,像一条日本金鱼。它拂擦我的心脏和膈,像拂擦鱼
缸的壁,它把淤泥从底部搅起。
那个被我夺去了嗓子的她,睁大眼睛瞪着我盼我说话。
然而我不知道该用那一只舌头对她说──是偷来的那只,还是早
已长在我口腔,过份良好的那只?
达文 译
摘自神话
最初是夜和风暴的神,一个无眼的偶像在那些蹦蹦跳跳的人面前,
赤裸、沾满血污。然后,在共和时代,就有许多神了。带着老婆、孩
子,吱吱嘎嘎作响的床,并无恶意地响着雷霆。到最后只有那些迷信
的神经过敏者,在口袋中装着风趣的小塑像,象徵是讥讽的神。那时
候已经没有伟大的神了。
然后巴伐利亚人来了。他们也看重那讥讽的小神,他们用脚后跟
把它踩碎,放进菜盘里。
达文 译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3372575805@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yuedu.yahoo001.com/shici/1764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