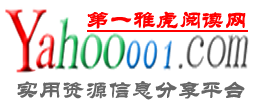总是醒在阳光里。眼帘外暖融融光灿灿的,小脸若花,一个笑使整朵花绽开,有细细的蕊,在花心,静静地望着我,我跟它,阳光里,面对面地。
手探入光线,变的彤红,指缝中一条金线化做无数条,我需要眯着眼,才能看清一些微粒飘舞在耀眼的光华中,臂,伸展开去,入了那缕桔红,感觉自己开成一朵深秋的菊。
祖母总是湿淋淋地回来。厚厚的黑棉衣服,糊满了新鲜的泥,深重的露,发间飘荡着一股热气,在进门之前,让我有些恍惚。仿若仙界里的神,头顶袅袅仙氲。
我家窑间,在那个永远不被光辉光顾的角落里,有一尊白瓷的菩萨,手扬柳枝,慈眉善目地被祖母的香火供着,每到初一十五,会有一些小吃食装在碟子里,摆在她的脚下,我的祖母做长长的揖,跪下去弯成一团,变得那样的渺小。
躲的她远远的,站在门槛上,看窑外,风从树尖上下来,卷了几片叶,在院子里嘻耍。
恐惧,像一根线,把我绕在中间,我坚信,哪怕一个些微不悦的念想都会被那尊瓷所识破,我只有站的远远的,不被她的视线所包围,才会遗忘因她带给我的压力。
当我的祖母以这样一个形象出现在深秋早晨的窑洞里的时候,我的确有些发怵。
队上分下来的掰玉米棒的任务,只有祖母一个人来完成。
这几天凌晨,祖母总会就着星光起来,穿上厚厚的衣服,坐到被露水打湿的田地里,一个一个地将那些带了包衣的玉米棒从金黄的秸杆上掰下来,堆成一坐金色的小山。
空气中弥漫着庄稼成熟的味道,嗅一口,入了心肺,清新而迷人。
当我扎好小辫出现在平展阔大的玉米田里的时候,太阳已上中天了。风从河床里呼啸着过来过去,偶尔将我的衣襟掀起,我笑着跑在颠簸不平的阡陌上,若一只欢实的鸟,叫声尖锐,身形矫健。
有浅浅的汗,在发间渗出,痒痒的,像谁用手搁将上去,轻挠。
阳光照着风中的温河,河水哗拉拉地流,夏天里那些鼓噪的蛙们在一夜之间安息。我躺在被风干了的秸杆上,跟祖母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泥土中腥的,厚的,黏的味道穿过厚厚的秸杆,入了我的喉鼻,在这一刻,我突然感觉到自己是土里生出来的娃娃,整个人,从里到外,都是泥息气,土滋味。
除了暗夜寒冷,如此广袤的家,如此自由的家,我在其中是这样的惬意而幸福。
我是那样地爱着泥土浓郁而多彩的气息,它中间有祖母的干草香,母亲的菊花香,父亲的热汗香,甚至还有妹妹的乳香,那么多那么多的香味,我都能从中分辨,从中体味,这些褐色的不明朗的泥土,令我迷醉,而留恋。
西山罩了一层艳红,整个村庄被包裹在落日的余辉中,谁家烟囱里冒着白茫茫的一缕烟,升腾在空中,与那些火烧云连在一处,成了画布上的景。
隔着长长的阡陌,隔着细细的风,隔着一些飘动的云朵,我听见来妮大爷在喊我的名字,一声声,上了河边的柳树尖,落下来,掠过归巢小鸟的翅膀,捎到我的耳边,我应着,有回声,远远地,在无名的石上,在未知的泥土的深处,回应着我。
祖母这时候正在拍打身上的草叶。裤腿上,一些暗色的,带了浅刺的植物试图悄悄地跟随我们回家,我把它们放在手心里,握住的时候,尖的刺微微扎上来,有一丝痒痒的疼痛。那一堆堆金黄的玉米,一条条暗褐的阡陌,还有阡陌的暗层下滋生的小虫,安静地注视着我们远离的脚步。
我被牵在祖母粗糙的手里慢慢向前。
远天的云彩,变换着各种各样的颜色和形状,祖母的脸,霎时彤红,霎时金黄。
面前沉静的村庄,残破的窑洞,坍塌的土墙,在风中落叶的树,还有没尾巴的小狗,在夕阳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美妙的光线所笼罩,幻成景,化成画,淹了我的眼,遮了我的眉,溶进我的心,而那些平展的,堆了小山般玉米的田地,也在这变幻无常的光线里,被岁月的快门所曝光,印成七彩的图片,定格在我记忆深深处,不褪色,不舍弃,难忘却。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3372575805@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yuedu.yahoo001.com/wenzhang/1775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