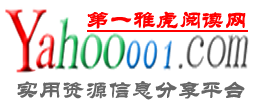他一生忙碌,却很寻常;他一生坎坷,却很勤谨;他一生侠义,却很正直;他一生孤傲,却很善良。
————题记
中秋薄幕,挂在窗外那一枚圆月,毫不吝惜地把白银般的月色散在书桌上,无限的秋思总会在冥想中摇曳——父亲就像一片云彩,忽走、忽飘、忽飞,不时地牵动着我昨日那并不遥远的怀想。[由整理]
十七年前的那个秋晨,父亲匆匆地背上他不知什么时候就准备好的行囊,挨个的将我们兄妹四人叫到他的跟前,例行地理解他每次出门前的训话。
尽管那时我们都步入而立之年和不惑之年,但父亲的威严,使我和弟妹都不敢有任何地怠慢。
“我就要远行了,是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你们无须明白我的行程,也无须打听我的归期。只是期望你们彼此珍惜手足真情,珍爱自已的家,要好好地善待你们的母亲。”
父亲就这样带着对世间的眷念,带着对亲情的眷念,踏上了那条落英缤纷,阡陌纵横的天堂之路。
他走得很从容,走得很干脆,甚至没有一点拖泥带水。望着父亲在晨雾中渐渐消失的背影,我哽咽地念叨道,父亲将在涅槃中进行一场坚苦的修行。
永川县(今为县级市)地处重庆市的西部,县城的北端是群山环绕的大安镇,沿着青石板铺成的山路再徒步38公里(当时交通十分闭塞,还没有公路)就是石庙村。
这是一个座落在大山深处的僻壤穷村,村子似一个覆盆,被巍峨盈盈,层峦叠嶂的花果山包裹得严严实实。
相传嫦娥曾到此山驻足时,便留下千般花卉,万种芬芳,花果山也由此而负盛名。
清澈甘冽的涧水从巉岩上湍流而下,总是绕着村户人家的门前淌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辛勤地滋养着这方土地。
父亲的根就在那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大孃瞒着母亲悄悄地把我从成都带回了石庙村(为此事母亲与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那时的母亲总有一种城里人固有的优越感)。
那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对于外面的世界除了陌生就是好奇。
当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呈此刻我眼帘的是一幕幕贫穷和凋蔽的景况。
村里的人过着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的生活,人们用呆滞、新奇的目光注视着来自大城市的陌生人。
我真不敢相信当时已成为共和国当家主人的川东人民为什么还过着如此贫困的日子,眼前的一切真让我难以置信。
望着风烛残年的大婆(奶奶的姐姐),我心生一种爱怜和愧疚,虽然我不能改变大婆的生活现状,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无疑是受到了一次极大的震撼。
我毫无保留地掏出临走时父亲给我做盘缠的5张一元的钞票塞进了大婆的围裙兜里,她半推半就地收下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看到大婆拿出一元钱交给盐贩买了一大包盐,然后她回过头笑着对我说,菜里已有几天都没有放盐了。
多少年过去了,我才渐渐地明白,父亲为什么会离乡背井,受尽磨难,独行江湖,不就是为了改变命运,与命运抗争么
有天晚上,大婆与我相坐在煤油灯下,她一边吸着水烟,一边摆起了父亲的往事。
父亲的原名叫刘茂祿,是读了几天私塾的爷爷给取的名。
在父亲出世后的五年里,老家连续遭遇水灾,整个庄稼几乎颗粒不收。
由于没有粮食,爷爷奶奶长期吞食“观音土”而患了水肿病,并相继去世。
年幼的父亲被寄养在舅爷家,到了父亲14岁那年,穷得只剩下一口铁锅的舅爷,对父亲的抚养已是无以为继了,而不得不把父亲送到驻扎在大安乡的国民党部队里,当上了“国軍”。
这支部队的最高长官是一位刘姓的团长。
虽说是行武出身,却是一位清风正气的儒将,他不仅仅饱读《四书》、《五经》,而且还擅长挥毫泼墨。
他见父亲聪明乖巧,做事又勤快麻利,便留在身边做了勤务兵。
父亲的名字也是在这个时候更改的。
“给我当兵,不要梦想到发财哦,我要你成为一个兵才、将才,就把`茂禄'改成`树良'吧。”
父亲听到这武断般的命令,只得点头应允了。
据父亲之后回忆,他跟随这位团长整整四年,除了干一些烧饭、端水、卫生、送信件等杂活,其余时间都是这位“老师”教他习字、识字、读书。
就是这样不经意的人生铺垫,却影响着父亲往后的几十年,甚至能够说从此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
1949年,父亲的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向解放军投诚起义,成都和平解放。
其所部被刘邓大军收编后,父亲也调入成都军区后勤部营房处任职。
1951年,部队奉命进驻西藏拉萨市。
父亲(左)参军时和战友的合影
在那段时光里,令他十分难忘的是,他亲眼目睹了年轻英武的达赖喇嘛(当时达赖只有17、8岁)来到部队慰问,还和他握过手;也见过当时还是农奴女的才旦卓玛,她经常到“金珠玛米”的驻地卖唱,父亲还为她送上了两盒压缩饼干。
1952年,父亲参加了著名的“昌都平叛”战役。
在一次平叛的途中,部队的运输车遭到了”藏兵“的伏击,父亲随车坠入深山峡谷,肋骨折断了三根,身负重伤,所幸的是捡回了一条命。
在成都治疗痊癒后,便留在了成都“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工作。
人的经历通常是日积月累的沉淀。
如果用几何图形把它标示出来,它并非是一条直线,而会出现许多拐点,倘若再把这些无数的拐点连接成一条直线,就不难看出他(她)人生经历的状态了。
父亲从点到线的经历让我惊叹、折服。
他凭着先天的睿智和超强的感悟、勤奋,其过人的才能已逐渐得到了充分地展现。
那是在国家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里,当时政府的财力还十分薄弱,軍费开支也极为有限,成都軍区后勤部又决定在简阳石桥镇修建部队营房,并把这项工程施工任务交给了父亲所在的单位。
父亲当即表示,由他来负责营房的工程设计,并推荐,建筑材料可就地取材,后勤的工作人员承揽建筑施工任务。
经过一年半的工程施工,顺利地完成营房建设任务,及时地解决了一个营建制的驻防需求。
要明白,当时父亲是仅凭着挎包里揣着的一本《砖混结构与房屋设计》的书籍,来完成这项承建工程的,这也是他独立完成建筑设计的处女作。
由于为部队节省了超多的财力,父亲在成都军区名噪一时。
1956年,成都軍区后勤部选送了10名优秀军官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学习土木建筑设计。
父亲得到了时任成都軍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炳炎上将的“钦点"(贺炳炎司令员还是父亲和母亲的证婚人)。
在这所高等学府里,他认识了人生中的第二位恩师——中国著名的土木设计专家陈辑教授。
在父亲的回忆里,他是这样评价这位建筑设计的泰斗:他有着四维空间的思维方式,重庆朝天门那错落有致的建筑群、府南河畔那绿水倒映的锦江滨馆、金牛山庄那石径幽幽的深深庭院都是他精妙绝伦的经典之作。
当年,父亲师从于陈楫教授就好比一位博导在带一个只具备基本运算潜力的小学生。可想而知,父亲的专业水平有多差呵,要如期地完成学业难度有多大呵,这都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毅力呵!
记得一位友人曾这样描述他当年是怎样考上“国防科技大学”时说,"为了摆脱祖祖辈辈的`草根'束缚,自已平日所付出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在读书学习时,往往都带着一种’阶级仇,民族恨'的强烈意识去激励自已。"因此,我想当时父亲的内在驱动力也是这样的吧因为他没有任何选取,只有学业有成,才能让命运出彩。
父亲凭着过人的天资和勤奋努力,最后完成了学业,已初涉到了土木工程设计的高端领域,在陈教授的脑海里也深深地记下了这个青年后生的名字。
1968年,父亲从部队转业到成都市青白江粮食仓库。在那个“深挖洞,广积粮”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父亲刚转业到地方就承担了修建青白江区人民医院的“地下防空医院”和青白江区人民武装部的“地下防空指挥所”的工程设计任务。
从现场勘察测量到施工图纸的设计绘制以及施工项目的预算、决算都由他一气呵成(如果按此刻的施工项目进行分工细化,则需要4——5个项目工程师来完成)。
个性是在解决人防工程中“渗水防潮”这一技术难题时,他力排众议,采用“排水疏导和二次沥青凝固法”,彻底解决了地下室防潮渗水的技术难关,使业内人士对他刮目相看。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又先后完成了红牌楼面粉厂“圆筒式立体仓”和"二仙桥粮食中转库"的工程设计工作,获得了当时中商部的“科技成果推广奖”。
除了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外,父亲的性格也颇具多面性。有时儒雅庄重,谈笑间总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时张扬无羁,让人感到虚实难辩;有时刚愎自用,却使身边的人尴尬为难;有时款款爱意,又能让子女们动容、敬重。
由于纵横交织的人脉关系和笃实的“精神资本”,父亲渐渐地养成了“二大爷”的作派,就连我们兄妹四人都畏惧三分。
直到有一天,我开始有点叛逆的主张时,并与他互打“顶张”时,他便会怒气冲天地对我嚷道:“在我的词典里,我文能安邦,武能定国”。
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大起大落的人。
在那里,还得提起一件事,一件至今都令我们兄妹四人感到遗憾和惋惜的事。
那是在我10岁那年(1968年),随着家庭的持续发展,生活矛盾也就不可避免的会摆在这个家庭的日程上。
年轻的母亲一方面要承担自己的本职工作,另一方面还要挤出更多的时间,花费更多的精力去料理我们兄妹四人的生活学习,以及照顾年事已高的外婆。
这些繁锁的日常生话无疑给这个刚起步不久的家庭带来极大的困惑和矛盾,也给正处于事业上升阶段的父亲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在这种背景下,父亲思考再三,只有脱下軍装转业到地方,才能成就这个家。
于是,他立即向所在的部队打了申请转业的报告。
由于部队当时急需父亲这样的专业技术人才,部队领导也纷纷出面给父亲做工作,劝其安心部队工作,组织会酌情思考家庭的具体困难。
此时的父亲哪里还听得进那么多的大道理哟,性子却一下就点燃了。他不顾多方劝阻,强行要求转业,并擅自联系地方工作单位。
父亲的做法,也大大惹脑了部队领导,并向父亲摊了牌:组织绝对不会向地方单位带给你的人事档案,如果不服从组织纪律就按复员軍人办理手续。
父亲一怒之下,拿到复员军人证明就到地方单位报到了。
多少年过去了,父亲不得不承认,他回到地方后,自己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那真是亏大发了。直到他去世,他的人事档案还留存在“西藏軍区驻川办事处”。
记得在他过世的讣告上是这样确定他的身份的:刘树良同志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工作、思想品德高尚、工作业绩突出、深受干部职工敬重的老同志。
在那里我要对父亲为了这个家庭所付出的心血、做出牺牲表示钦佩。同时,也为他似锦的前程感到深深地痛惜。
写到那里,原本想用浓重的笔墨来书写一下他与母亲这辈子的爱意情事,但疏于手中掌握的相关素材少之又少,而无从着墨,实感遗憾。
只是略微明白一点皮毛,父母的恋情颇有“罗曼谛克”式的浪漫,可谓是美丽的邂逅。
年轻时的母亲,是典型的川北美女,白晢的肌夫把俊俏的面容彰显得高贵优雅,弯弯的眉下嵌着一双澄澈如水的大眼,两条乌黑的长辫搭在肩上,走起路来左右摆动,更是妩媚动人,在熙攘的人流里总有极高的“回头率”。
虽然,父亲没有透露当年是如何俘获芳心,抱得美人归的情史,但至少有一点能够肯定,他们的婚姻成就了执手偕老的幸福,也成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幸福!
在孩提时,我的一招一式都承袭了父亲的基因:喜读书、善勤思、求进取、笃自信。
小学三年级时,我就偷偷地把父亲收藏在衣柜里的《儒林外史》、《三言三拍》、《三国志》、《七侠五义》、《济公传》(当时在“文革”时期,这些书籍都视为是十恶不赦的禁书)都阅读了一遍。在日后的习作和语言表达上都受益匪浅,并初步掌握了旁证博引,引经据典等学习方法,父亲甚为高兴。
个性是在我成人后,幵始涉世时,他又经常把我带到武候祠,给我讲释三国时期历史人物的文韬武略。
从"两表酬三顾,一对足千秋"的诸葛孔明到“既生亮,何生瑜”的英才少年周公瑾;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乱世英雄曹孟德到“三顾茅庐”,求贤若渴的刘皇叔。父亲好似在说书一般侃侃道来:时而“乱石穿空”,时而“惊涛拍岸”,让我听得如痴如醉。
当然,最受他推崇的当数清人赵藩撰写的《攻心联》。上联是:能攻心者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之后治蜀要深思。
坊间里传,1958年,毛主席来到成都武侯祠,在这幅对联下伫立良久,感慨至深。
“文革”时期,刘兴元从广州调至四川军区任司令员,毛主席让他到四川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武候祠观赏《攻心联》。
由于饱受动乱之苦的巴蜀大地,已是满目疮痍,百疲俱兴,人民更需要休养生息。也许是得道所悟,在刘入川后,动荡得到了遏制,国民经济渐呈复苏的态势。
能够这样说,我的做人之本,处世之道,在这个时期已具雏形了,父亲不愧是我的良师益友。
父母亲和我的女儿
当我的爱女还不到4岁时,他又怀抱她到武候祠理解“三国文化”的熏陶,似乎他在提醒我,为了她的将来,你“务必从娃娃抓起”(邓小平对中国足球未来说的话)。
“玄蝉去尽叶落黄,无边落木萧萧下。”秋,已渐渐的深了。大地写着萧瑟的孤独,天边揮洒着淡淡的闲云。
我停下手中的笔,久久地伫立在窗前,忽然想起爱妻说的那句话,阴阳相隔十七年,亲人是越走越远了!内心顿似一阵痛楚的悲凉,难道生命的底片是这般伤感?懂事的女儿在微信里会意地对我说:只要感情里还盛着往事、回忆、问候,就能触摸到爷爷的温暖、欢笑。
女儿真把我心思给读透了,所谓灵犀相通,当此际,有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彻悟。
尽管天各一方,却是流年似水。生者的灵魂得到了沐浴、升华,而逝者也得到了炼狱、超度。承父亲在天之灵,如今我们这个大家庭日益兴旺,洪福吉祥。
母亲自是安康幸福,乐在其中;女儿已是亭亭玉立,落落大方,她不负爷爷的厚望,已在世界名校获得博士学位,可谓是光宗耀祖呵!其它后生们也都出类拔萃,前途无量。
恰如,我家三妹手执佛珠,坐于蒲团读经诵道:“这些都是父亲祈福、天祐的善报。”
我诚愿这祈福和天祐永远伴随着母亲和我们一生。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3372575805@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yuedu.yahoo001.com/wenzhang/2214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