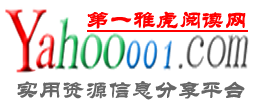也许小时候爷爷太过宠爱我了,爷爷去世都五十多年了,他那音容笑貌还时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种幸福感绵远悠长。今天我想用粗略的文笔,写下爷爷晚年的苦乐趣事儿。
——题记
农村有句古话,叫人活七十古来稀,爷爷是村上年纪最长,辈份最高,有着很高威望的倔老头儿。
印象中,爷爷瘦高个儿,留着长长的山羊胡儿,眼不花,耳不聋,象树皮一样的脸上,布满了沧桑,满口的牙齿不知道什么时候,都下岗了。八十多岁了还有着的倔强的脾气,很任性。爷爷有个形影不离的伙伴儿,就那是个“柱人为乐”的漂亮拐棍儿,其实也不值钱,就是一根木棍儿,上边带个拐弯弯的手把儿,被爷爷的大手磨得如碧玉一般流光华润。
爷爷一辈子只和土地打交道,没出过远门儿,老年最大的兴趣,就是上街赶集,看看人烟,和老朋友聊聊天儿,看看街头玩猴儿打耍的,给自己找点乐子。爷爷赶集的时候,一出门就把拐棍往那后腰间一横,两手攥住拐棍两头,哼着不着调儿的小曲儿,雄赳赳气昂昂。
爷爷膝下有四个儿女,我的两个姑姑,伯父和父亲,父亲是他最小的儿子。奶奶去世的早,中年时的爷爷带着全家,从老家水星赵来到现在的官庄,给地主家种批子地(按产量分成)租住地主家的房子,辛苦了大半辈子,依然田无一垄,房无一间,一直到解放时候,才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和房屋。
伯父和父亲一直没有分家,还有大姑也在家里住,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姑夫参加了皇协军,不到半个月就被枪打死了,大姑二十四岁就守寡,在婆家被人唾弃和欺负,就带着表哥住回了娘家,这一大家子人在爷爷的领导下,还算和谐。土地改革的时候,表哥已经长大成人,大姑才和表哥一起回了自己的家,伯父也和父亲分了家。
分家时爷爷已经七十多岁,住在我们家里,吃饭就两家轮着,这让爷爷很纳闷儿,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大姑不会做饭,爷爷说大姑蒸的馒头象牛屎铺摊儿,擀的面条象豆茬,根本挑不起来。大姑也只能摘菜打下手,伯母烧锅,擀面条蒸馒头炒菜都是母亲的,这一分家,爷爷可闹心了。前半月在伯母家吃饭,其实伯母很善良,也很孝顺,就是人太老实,手脚有点拙笨,说话也不怎么利索,不会做饭,就连玉米糝子都磨不好。别小看磨糝子,那可是一道技术活儿,把磨过的玉米,放在面罗里,两只手端着罗,一手用力轻,一手用力重,转圈晃动,一直转的玉米皮子全部集中在中心部位,才用手轻轻地抓出来,然后再磨,需要好几遍儿才能抓净,糝子磨得细,皮儿抓的净,摸着手感好,看着金灿灿的,熬出来的饭才又香又粘糊。伯母怎么都学不会,磨的糝子又粗又大,又有皮子,涩拉拉的,爷爷咬不动,也咽不下去,特别晚上吃面条,爷爷一端起碗,就长吁短叹,用筷子挟着一根面条儿忽闪几忽闪,摇摇头无奈地说,这哪是面条,就是铡钉(铡草刀上穿的指头粗的铁钉)能砸折鼻梁骨,说完把碗一放,气呼呼地去睡觉了。说的伯母两眼泪丝丝的,为此伯父常常咬着牙跺着脚骂伯母不中用。母亲看爷爷不高兴,赶紧做好饭,把第一碗饭端给爷爷,轻声对爷爷说,爹,您别生气了,您在那儿吃不好,就回来吃。爷爷接着象丝窝儿一样香喷喷的面条,舒心地笑了。
爷爷轮着吃饭,也只是个形式,母亲总担心爷爷在伯母家吃不好饭,大多时间都还是在我家吃,每逢爷爷过生日的时候,母亲提前几天都念叨,到了生日那天,母亲一早起来,第一时间给爷爷煮几个鸡蛋,中午做肉臊子长寿面,在那个穷苦年代,爷爷感到非常幸福,母亲忙于家务,偶尔也会把爷爷的生日忘记,等想起来时赶紧煮好鸡蛋,拿到爷爷面前并给爷爷道歉,爷爷高兴地双手接过鸡蛋,脸上笑开了花说,忘生儿好!忘生儿好!咱能越过越旺了。
爷爷是个偏心眼儿,轮到伯母家吃饭的时候,集不集都要上街转一圈,回来就睡觉,轮到我们家的时候,精气神就来了,吃完饭就帮助父亲干活,到了秋天,收罢秋庄稼以后,爷爷也不要拐棍了,吃完饭就背着他的鹰爪儿(两个齿的耙子)去刨芝麻茬,棉花茬,然后捆得整整齐齐的,用鹰爪儿把穿着柴活捆,背到肩上,步履蹒跚的回家,母亲看着满头大汗的爷爷,心疼地说,爹,您老儿别去干了,咱家不缺柴烧,让别人看见了,会以说我不孝顺您呢!爷爷眼一瞪说,我高兴,谁敢说我掰他牙。一秋天的辛苦劳动,爷爷住的一间房子,除了他的床,垛满了柴火,一直挨着房顶。
冬天,没有了绿色的陪衬,显得一派破落凄凉,只有袅袅炊烟弥漫着村庄。增加了丝丝温良,我们家门前堆了一个小山一样的土堆,那是生产队垫牛铺用的土,晴天的时候,爷爷最喜欢晒太阳,穿着母亲给她做的黑蓝色的厚厚的长袍子,棉袜棉靴,双手的手指交叉枕在脑后,眯缝着眼儿,翘着二郎腿,靠在背风向阳的土堆上,晒得暖洋洋汗津津的,小弟弟趴在爷爷身上,给爷爷捋捋胡子,甭提爷爷有多高兴。
小时候总觉得爷爷很有钱,小布包儿里一沓儿一沓儿的,常带着我上街买好吃的。卖油馍和卖包子的老板一看见爷爷,老远都打招呼:二伯好哇!您老儿又带着孙女儿赶集了,爷爷笑呵呵地答应着,把那用布裹一层又一层的钱,小心翼翼地掏出来,递给人家说,给俺串串儿包子,隔一天油馍,隔一天水煎包儿,爷爷一次都舍不得吃,原来那是伯父家三个哥哥孝敬爷爷的钱,爷爷舍不得花,都让我给吃了。
三年自然灾害中,爷爷可受苦了,那时候农民都吃食堂,不准自己做饭,每年荒春时节,食堂就分点煮熟的高粱籽,爷爷咬不动,只好用蒜臼把高粱籽捣碎吃,高粱很涩,年轻人还勉强凑乎,老年人吃了就拉不下来,爷爷瘦得皮包骨头。大旱之年,蝗虫多,我们叫它蚂蚱,铺天盖地,爷爷想了个好主意,薅了一些青麻杆,用他那象枯树一样的老手,编了几个小篓篓儿,用剪刀把烂鞋底子剪成两半儿,用锥子钻点小窟窿,用针线把小木棍儿连在半截底子上,蚂蚱拍子就做成了,爷爷带两个小弟弟,去逮蚂蚱,我去剜野菜,别看爷爷八十多岁了,手脚儿还挺利索呢,半晌的时间,蚂蚱娄装得满满的,有大老扁,过冬飞,有老飞头,等等,大老扁长得很好看,圆长的肚子,扁扁的头,长着双层的翅膀,上边一层是青绿色,下边一层象蜻蜓的薄翼,金黄透亮,飞得很快,长圆肚子,小时候是绿色的,长大了变成黄色,一肚子的卵子,它一产卵,生出几百个小老扁儿女。过冬飞长着雄壮威武的身躯,呈暗褐色,飞起来嗖嗖的带风,飞不太远,它能藏在很隐蔽的地方越冬。老飞头有大有小,有暗褐色的,也有黄绿色的。回到家里,爷爷把它们倒在地上,哇!一堆的蚂蚱乱呱拥,有的还想试图逃跑,爷爷用他长长的指甲,先把它们一个个翅膀掐掉,然后再把头拽掉,带出一滴流肠子,场子里边全是屎,蚂蚱头喂了小鸡儿,蚂蚱肚儿,放在水里洗干净,没有油,就放点盐炒一炒,炒的黄澄澄燋露露的,香气四溢,闻着就让人垂延欲滴,我们吃得很高兴,爷爷干瞪眼,只得把他的蒜臼搬出来,把蚂蚱捣成面儿,吃的那个香啊!爷爷没牙嘴漏风,吃着掉着,一只手往嘴里填,一只手在下边接着,胡子上粘的都是蚂蚱粉,爷孙四个吃着笑着,把爷爷笑得都不好意思了。农村有句俗话,叫蚂蚱只活八个月,一霜打个直拉觉(一下霜蚂蚱就被霜打死了)从春天到深秋,爷爷一直带着弟弟们逮蚂蚱吃,慢慢的爷爷的身体也健康了,脸色也显红润了。
为了帮助孙子们渡过灾荒,爷爷在河边儿刨了一块地,种了很多梆姜,梆姜长得很高,叶子像向日葵,又比向日葵叶子瘦,繁殖的很快,果实在地下,和生姜长相差不多,比生姜个儿大,麻麻的,不能生吃,只能煮熟或者烧熟了,吃着甜甜脆脆的,吃多了会反胃,只能救一时心慌。邻居家的孩子们,饿极了都会去扒点烧烧吃。
我们家乡人常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句还还真应在了爷爷身上,好不容易熬过饥荒年,生活刚刚有所好转,我上五年级那年,阴历二月的一天,是星期天,爷爷和往常一样让我和他一起上街赶集,爷爷逛街,我就去了学校做作业,一会儿的功夫,有人去叫我,说爷爷被汽车轧了,我象疯了一样哭着喊着,跑到爷爷身边,爷爷躺在地上,左脚被汽车压掉半拉,鲜血直淌,那半拉脚粘在了汽车轮胎上,碎了,好心的人们,把爷爷抬到街上的卫生所,让吕医生给爷爷包扎伤口,他们告诉我说,你爷爷太倔了,汽车过来的时候,别人拉着他说,老先生,汽车过来了别走,爷爷就象没听见,径直向前走,刚迈出左脚,就被压上了,其实那时的汽车非常少,偶尔才会过一辆,就是这偶尔的一辆,正好伤到了爷爷。是爷爷的倔犟还是天意,谁也说不清楚,看着爷爷痛苦的样子,我真是肠子都悔青了,我不该丢下爷爷去上学校,我哭得伤心极了。
同村的人回家捎信儿,爷爷的脚包扎好,父亲他们也抬了个门板来了,铺上被子,把爷爷放到门板上,抬回家了,伯父和父亲也不会讹人,让人家把车开走了。回到家里,爷爷疼痛难忍,逼着伯父去给他买藤黄(一种有毒的药)想一死了之。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爷爷的伤日渐好转,脚上也长出了嫩嫩的肉芽,每天放学我就坐在爷爷的床前,陪爷爷说话,给爷爷捋捋胡子,爷爷张着大嘴笑着说,我好了还能去上街赶集。就在大家充满希望的时候,爷爷突然高烧不退,医生诊断,爷爷患上了破伤风,慢慢的神智昏迷,口齿不清,两个月后的四月十二的晚上看着爷爷情况不好,一家人都没睡觉,守在爷爷身边,到了大约五更时分,爷爷带着对儿孙的不舍,口中模模糊糊呼唤着我小弟弟的名字,波——波——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在儿孙们地目送下,灵魂缓缓升入了天堂,享年八十四岁。
爷爷最大的梦想,是能亲眼看着我考上初中,可爷爷没能等到那一天,由于我的疏忽,爷爷的死,也给我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3372575805@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yuedu.yahoo001.com/zuowen/331753.html